伏牛山的晨雾还没散尽,德昌叔已经蹲在洛河滩边挑石头了。青布鞋踩在潮湿的鹅卵石上发出咯吱轻响,他弯腰时露出后颈一道蜈蚣似的疤,那是十三岁学熬汤时被锅沿烫的。师父用艾草灰摁在伤口上说:“这是汤印,没这道印子镇不住老汤里的火气。”河风裹着水腥气掠过,他掂起块带青纹的卵石对着天光瞧,石面上蜿蜒的纹路像极了太爷爷那本《汤经》里的蝌蚪文。
妞妞背着柳条筐跟在后头,七岁的小脚丫专挑有青苔的石头踩。“爷爷,这块会唱歌哩!”她举起块中空的石头贴在耳边,里头传出呜呜的风声。德昌叔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成一簇野菊花:“中,这是被洛河娘娘亲过的石头。”话音未落,河对岸突然传来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三辆贴着“网红探店”标语的越野车碾过麦田,惊飞一群啄食的麻雀。妞妞攥紧爷爷的衣角,德昌叔眯眼望着车身上“科技赋能传统美食”的荧光字,把卵石重重扔进竹篓,惊得篓底两只蟋蟀跳进了河边的芦苇丛。
回程路上遇见村会计老刘,他正站在烩面馆门口跺脚:“德昌哥,市里来的调料商等你半个钟头了!”穿皮夹克的男人跷着二郎腿坐在八仙桌前,银色金属箱里五颜六色的瓶子折射着冷光。德昌叔不紧不慢地把卵石码进灶眼,二十七个凹槽嵌得严丝合缝。百年杉木锅盖一掀,混着禹州黄姜和伏牛山花椒的羊骨香轰地蹿出来,把墙上的灶王爷画像熏得更黄了。
“这瓶抵得上您熬三天汤。”男人拧开瓶盖,异香瞬间盖过满屋醇厚。“增稠剂能让面汤挂勺,保水灵保证羊肉三天不柴……”铜勺突然敲在铁铸关公像上,“当啷”一声震得香灰簌簌往下落。德昌叔的嗓门比洛河汛期的浪头还响:“中州大地的滋味,不在这些个化学仙丹里!”
玻璃门外闪过一团红光,穿超短裙的女主播举着自拍杆旋风般闯进来。“家人们快看!这就是全网悬赏十万寻找的顽固老头……”手机镜头刚对准沸腾的老汤,德昌叔抄起葫芦瓢舀起滚汤,手腕一抖泼在青石门槛上。青石腾起三尺白烟,惊得女主播高跟鞋崴进砖缝。“俺这规矩,头锅汤得敬河神!”
冬至头锅汤开张那日,穿貂皮的女人甩出黑金卡要包场拍带货视频。德昌叔瞄了眼她身后举补光灯的团队,汤勺往青石台面一磕,暗红石面上二十八道凹痕微微发亮——都是历年拒绝包场时敲出来的。“头碗汤得先敬河神。”他舀满粗瓷海碗,稳稳泼进门外洛河。碎冰撞着滚汤嘶嘶作响,白雾里恍惚有个戴斗笠的老汉颔首。光绪二十六年黄河决堤,太爷爷把最后一锅汤料绑在门板上,自己变成河伯庙里的泥胎,手指头还保持着撒香料的姿势。
开春时修高速路的推土机轰到村口,德昌叔却在后院起新灶。九十九口钧窑陶瓮埋进三丈深的黄土坑,瓮里封着去岁的陈汤。包工头叼着烟冷笑:“老头,你这破灶值我推土机半天工钱不?”“汤魂入地三丈,接的是伏牛山的地脉。”德昌叔往坑里撒朱砂,混着妞妞采的二月兰花瓣。小丫头跪在坑边唱祖传的歌谣,童谣惊起槐树林里的灰喜鹊,叼走了施工队安全帽上的红飘带。
惊蛰夜雷劈了村口“非遗美食街”的霓虹招牌,德昌叔的柴火灶却在老槐林里支起来了。百年树根盘成天然灶台,妞妞踮脚往沸腾的老汤里投新采的槐叶。网红们举着手机围过来,镜头却被蒸腾的水汽蒙住——那雾气凝成凤凰形状,绕着老槐树转了三圈才散。穿中山装的老者颤巍巍捧起汤碗,忽然老泪纵横:“五十年了,这汤里还滚着洛阳水席的魂呐!”他指甲缝里嵌着龙门石窟的灰土,衣襟上“民俗协会”的银章被老汤热气熏得发亮。
谷雨那日,德昌叔带妞妞去采头茬槐花。小丫头忽然指着老槐树喊:“爷爷看!树流泪了!”树干裂缝里渗出的琥珀色树脂,在阳光下泛着老汤般的光泽。黄昏时分,穿校服的少女走进店来,胸牌上“黄河流域民俗保护专业”的字样被夕阳镀了金边。
“能尝尝活着的文物吗?”女孩眼睛亮得像是揉进了洛河里的星星。德昌叔往汤里多撒了把崖柏叶,看着蒸汽在她睫毛上凝成水珠。店外忽然响起汽车轰鸣,那些“科技赋能”的越野车掉转车头,朝着快倒闭的网红美食街仓皇逃去。老槐树的影子爬上青石柜台,二十七个灶眼里的卵石在余烬中轻微爆响,应和着妞妞新学的歌谣:“黄河水,伏牛山,老汤滚沸百年传……”
洛河水静静淌着,月光给老汤锅镀了层银边。黑檀木匣里的《汤经》悄然翻页,末页太爷爷的血字在夜色中泛着微光。穿校服的少女掏出笔记本,扉页上工整誊写着:“味道是流淌的文明,守味人皆是历史的摆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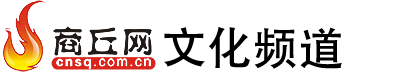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