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
梅雨落下的第一日,檐角的瓦当便开始唱歌。雨水顺着黛色沟壑蜿蜒而下,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珍珠。我总爱趴在雕花木窗边数那些水珠子,一颗两颗,数到第七颗时,外婆的竹簸箕里就盛满了新摘的栀子花。湿漉漉的香气漫过门槛,缠绕着八仙桌上那盏永远温着的红枣茶。
南方的雨季是青苔的盛宴。墙根下的地衣裹着细密的绒毛,像老裁缝珍藏的绿绸缎,一寸寸往石阶上铺展。外婆说苔痕是光阴的脚印,她总在雨势渐小时披着棕蓑衣,用竹篾子刮去门框边的苔藓。可那些碧玉般的小东西倔得很,夜里窸窸窣窣地踮着脚跳舞,天明时又在石缝间探出圆润的脑壳。我常把指甲盖大的青苔养在青花碗里,看它们蜷缩成墨绿的绒球,又在水珠浸润下舒展成星星的形状。
木楼梯的吱呀声总在午后响起。母亲把褪色的蓝布衫铺在膝头,银针拖着丝线穿过补丁,针脚比雨帘还细密。她补衣裳时爱哼《茉莉花》,声音被水汽洇得绵软,像灶膛里将熄未熄的灰烬。我伏在她膝头数瓦当垂落的水珠,七颗便是一轮,檐下的铜风铃叮咚作响,把光阴切成薄如蝉翼的片段。
雨下到第九天,后院的老井漫出青雾。井栏上生着乳白的菌子,外婆用银簪子轻轻一挑,菌伞便簌簌落进竹篮。她说这是土地爷赏的素馄饨馅,配着新磨的豆腐煮汤,能祛三伏天的燥气。我蹲在井沿看自己的倒影被涟漪揉碎,忽然有冰凉的小东西蹭过脚踝——是井底的青虾顺着水草游上来,透明的须子拂着井壁的苔衣。
巷口的石板路在雨季会长出眼睛。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痕,像老人掌心的纹路里藏着陈年旧事。卖菱角的阿婆戴着竹笠经过,雨鞋叩击石板的声响,与远处寺院的钟声在雨雾中相撞。她筐里的红菱角沾着淤泥,掰开后却露出雪白的芯子,甜味里掺着水草的腥气。外婆总用旧报纸包了硬币换菱角,报纸上的铅字在雨天洇成团团墨梅。
最喜骤雨初歇的黄昏。西天撕开道金红的裂缝,光瀑倾泻在滴水的瓦楞上,蒸腾的水雾里浮动着七彩虹桥。我赤脚跑过沁凉的石板,看积水洼中游动的云影——那是被雨水泡软的棉絮,是龙王爷打翻的胭脂盒,是外婆故事里偷溜下凡的织女遗落的纺锤。墙根的苔藓吸饱了霞光,绿得能拧出汁来,蚂蚁排着队搬运溺亡的蠓虫。
雨停了又落的日子,堂前的燕子孵出雏鸟。黄喙的小家伙们挤在泥巢边,绒毛上缀着水珠,像裹了糖霜的糯米团子。老燕子掠着水面衔来蜉蝣时,雏鸟的啁啾声便裹着青苔气息漫进窗棂。母亲在燕巢下悬了块蓝印花布,说这样能接住坠落的幼雏。果然有回跌下只翅膀未硬的,在我掌心扑腾如跳动的水滴,待羽毛干透又箭矢般射向云端。
二月将尽时,苔痕已攀上第七级石阶。外婆取下悬在梁上的艾草束,混着晒干的柚子叶煮水,说这是送别梅雨的药汤。滚烫的艾香漫过天井,廊下的青石板浮起朦胧的蒸汽,恍若时光倒流的河。我忽然看见多年前的母亲坐在相同的位置补衣裳,发间别着新鲜的栀子,而更久远的光阴里,或许还有个淘气的小男孩,正踮脚采摘井沿的菌子。
今晨推开斑驳的木门,石阶上的苔衣已结成厚毯。梅雨季遗落的种子在缝隙里生根,竟开出米粒大的紫花,像是大地缝制的碎花裙裾。外婆留下的青花碗仍在窗台,碗底的苔藓年年枯荣,而八仙桌上的红枣茶永远温热,水汽蜿蜒成新的沟壑,在岁月里酿出比栀子更醇厚的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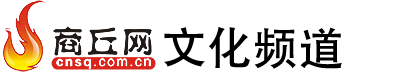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