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玉笙
天生万物,皆有人爱。爱源自缘分,一旦有缘,便难舍难离,哪怕它是一张床板。
说起这张床板,它就在我的书房里。书房里有一个单人床,最下面的床板宽90公分、长2米、厚2公分。上面尽管有褥子、床单覆盖,可仍旧挡不住这张床板透出来的温度,还有硬度。我不清楚它是不是胡杨木,但知道它绝对产自新疆。
我与这张床板有缘,是因为我是在新疆长大,在新疆步入社会的。1974年6月的一天,我和四十多个初中、高中毕业的同学打着红旗、唱着歌,从新疆石河子“工四团”出发,步行到天山脚下的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准确地说,是到一个连队,大家都习惯地称它为“农一连”。到了地方,连长、指导员致了简短而又热情的欢迎辞,我们这一众男生便被安排到一个大菜窖住下。
当时,连队除了给知青们配备劳动工具,还给每个人准备了一张床板。那床板背面有三根硬衬,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发给我的这一张是由四块板子拼成的,挺沉。
那时,我们都还小,也就是十七八岁那样儿。一群毛孩子刚离开父母,做起事来顾头不顾腚。好在各人有各人的床铺,像是“私人领地”。床头上挂满了衣物、水壶什么的,横七竖八,杂货铺似的。有的同学对此颇有怨言,认为这太寒酸了。可一听老一辈农工讲起农场初创时期住地窝子、睡大铺时,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农一连的“军垦战士”来自各省市,还有上海、天津等地的知青。他们有的在农一连已经是第二代了。戈壁荒滩的绿洲,就是他们“边疆的家园”。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产生了万千感慨,业余时间动笔记录下所听到看到的一切。写作时没有桌子,就趴在床板上划拉。自己认为可以了,便工工整整地誊抄在稿纸上,装入信封,贴上八分钱邮票投寄出去。但投出去的稿子都是“泥牛入海”,渺无音讯。由此,同学们善意地讥笑我、讽刺我,我听到了也不在乎,只是笑笑。我想,反正看书写字总比打牌闲聊好。这也是个人爱好、兴趣所致,谁也挡不住。到了冬季,连队搞土地平整,大家冒着严寒到大田里热火朝天地苦干,眉毛上、帽檐上都凝着白花花的硬霜。指导员找到我,用他那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说:“小司,写一篇广播稿呗,鼓励鼓励大家!”
于是,回到“寝室”里,我趴在床板上写了一篇《不畏严寒平整土地》的稿子,交给指导员审阅。很快,这篇稿子在连队大喇叭上播出,还是指导员亲自念的。这让我美了好多天,同学们也对我刮目相看,有的还打来开水让我喝。可美中不足的是,指导员将稿子念得磕磕巴巴的,个别字还念错。事后,指导员见了我说:“小司,你那篇稿子写得不错,就是有的地方文绉绉得不上口。”此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再写稿子时注意多用大众化词句。
得益于我爱好读书和写作,1975年夏天,我被团部选定为“后备教师”,集中培训两个月后,分配到独山子一营子弟学校当五年级语文老师。临报到时,我将那块床板也带上——这是我的“书桌”啊!
独山子一营子弟学校的条件自然比农一连好,可我还是喜欢肘撑在床板上看书写稿。同事们奇怪:“有桌子不用非得恋床,何苦?”
我戏言道:“习惯了,这样很容易找到灵感。”
1976年1月,我入伍到南疆基建工程兵某部当了一名战士。临别时,我让父母把那块床板放好,回来我还要用。母亲笑笑,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1978年我父母调回河南老家,他们来信说:“那张床板给你带回来了。”读到信,我好像看到了那张床板,激励我写了一篇又一篇稿子。其中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8月的《解放军文艺》上,标题是《最后一个早晨》。这是我见刊的“处女作”,由此,再也停不下笔。
1979年我复员回到父母身边工作,见到了这张保存完好的床板,抱起来又是打转又是亲吻,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从此以后,这位“恋人”就没有离开过我,或者说我离不开它。即使结婚以后,我也喜欢睡小床,清净。
2016年夏,我偕妻去新疆旅游,石河子“农一连”旧址自然是首选。几十个春秋过去,这地方完全变了模样。放眼望去,果园连片,郁郁葱葱;瓜果飘香,沁人心扉。由于盛产甜蜜的蟠桃等水果,被当地人称之为“花果山”。询问路人,皆不知“农一连”。也难怪,这些人都是从内地来此承包果园和大田的,怎么能知道其“前身”?在旧址上来回徜徉,竟然找不到当初我们知青栖身的大菜窖。我对妻说:“都没了哩,幸亏我还留有那张床板!”
从新疆回来后,我对这张床板有了新的感知:它留下了我知青生活的气息,保有了那个时代的温度。不管时光如何流淌、时代怎么变化,有一张好床板作伴,青春的记忆就不会褪去。
有时掀开铺盖,细看它美妙如画的纹路,想象它几十年前还是一棵大树的一部分时,曾给这世上贡献了多少氧气和绿荫,用其挺拔的身躯挡住了多少凛冽的风沙?变身为床板后,又托举了我人生大部分睡梦,不仅给了我灵感,还给了我无限的遐想和启迪,缘分啊!
冥冥中,我似乎听到了床板发出的声音。那声音来自远方,又像是来自附近。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别看它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只要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陪伴你,你就会觉得生命之旅有了不平常的意义,珍惜它、敬畏它,其实就是珍惜、敬畏生命。也许,它的“生命”比自己还长久。于是,每想到此,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句——
谢谢你,我的新疆床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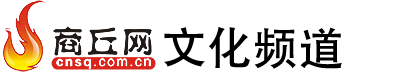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