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1992年,小镇的夏天,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在老街打听一个人。她似乎是在踮着脚向前探路,远看起来,她就像一只小鹿在轻盈跳动。
这个来自湖北一座县城的女孩,与我所在的小镇相距130多公里,她首先乘坐长途客车,再坐摩托车赶到小镇。女孩要打听的人,就是在小镇一家单位工作的我。女孩留着当年流行的山口百惠发型,齐眉刘海,肌肤嫩白。她打听到了我的单位,直接敲响了我寝室的门。那是一个周末,我正伏案写作,生长旺盛的胡子也懒得刮。女孩问:“你就是李?”我点点头,心头有些恐慌。她莞尔一笑,居然还有两个小酒窝。女孩告诉我她来小镇寻我的来由——原来,她从一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大量随笔。这引起了她的关注。通过与编辑部联系,打听到我的地址,于是寻我而来。
那是一个文学发烧的黄金年代,小镇上彩色电视机还没普及,有一家报刊亭出售报纸与杂志。报纸与杂志上,常常有我的文章出现。但墙内开花墙外香,我这个文学青年并没有引起小镇居民们的多大关注,倒是小镇首富牟裁缝看上了我这个神情忧郁的青年,几次托人要把他的独生女许配给我。牟裁缝甚至亲自来过我单位几次,拐弯抹角说了一些话,我已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牟裁缝还托人转告我,他就一个女儿,今后留下的家产都归她女儿和我。牟裁缝去补了2颗闪闪发亮的金牙,一开口说话就明晃晃地刺眼睛,令我特别反感。倒是我父亲很着急,他得知消息后对我直来直去地说道:“像你这个情况,天天写年年写也写不出一个啥名堂。单位好像也没心思培养你这个作家了,还不早点结婚,恐怕就成一个单身汉了。”父亲那年55岁了,头发花白。他急着想抱孙子了,在路上看见别人家的小孩,也会忍不住去抱一抱,甚至亲热地抱在怀里用胡子去扎小孩的脸蛋。有天父亲还严肃地告诉我一个数字,说是我们这个县,男女比例失调,大致是100个男人里面就有8个要打光棍。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寻来的一组数字,但他的说法还是让我受到惊吓。
那天,这个外地来的女孩告诉我,她是那个县城的小学老师,很是喜欢我的文章,经常把我的美文大段大段地在小河边背诵。女孩试探性地问我,怎么,今天你的女朋友没来陪你啊?我直接回答,还没有。其实那年我已心仪县城女子柳,只是她家里人还有些嫌弃偏居小镇的我。她母亲有个雨天悄悄来到泥浆四溢的小镇,回去后跟女儿感叹:“哎呀,小镇那个环境,你消受不了的。”女孩得知我还没女朋友后,似乎来了精神,几乎是直接表达了。她说很爱慕我的才华,自己还没恋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人。一会后,她似乎对自己的不诚实有些过意不去,告诉我,她有过一次恋爱,但对方太俗气了,对她喜欢的文学不感兴趣,两个人在一起是喝咖啡与吃大蒜的差别。
中午,我请女孩在老街一家吊脚楼饭馆简单吃了饭,肥肠扣碗、荷叶蒸肉、米豆腐汤。她仰头问我:“你喜欢啥女孩?”我回答,林黛玉那种女子。早些年,我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对林黛玉以及扮演者着迷。
饭后,我们又来到小镇河流上的老石拱桥上坐坐,凉风徐徐,桥下河水潺潺。恰好牟裁缝路过,他这次没露出金牙对我笑了,神情古怪地匆匆而过。女孩突然捂住胸口咳嗽,轻喘微微。神经敏感如雷达的我感到,女孩似乎在模仿林黛玉的咳嗽。
一周后,我在小镇收到了女孩从她那县城给我邮寄来的信件,字迹娟秀。在信里,女孩的心事,全部托付给我了。她说,她要与我恋爱,同我结婚,她相信我的才华能够换来美好的生活。
后来,她又连续来了3次信。我一直没回信。我这个对感情有些偏执的人,是宁愿把自己吊到一棵树上憋死的。
1994年秋天,我与爱慕的柳姑娘在小镇结婚了。打动柳姑娘的,依然是我的那点所谓文学才华。
30年的时间过去了,日子在油烟滚滚、缝缝补补中溜过去了,光阴的河流有温情脉脉的涟漪,也有大量沉渣泛起。我们的家,朴素、简单,在城里灯海下,甚至找不到它那一扇窗口发出的光。牟裁缝家的女儿女婿家,据说而今身家都已上亿了。我,一个小作者,业余用文字换来的一点报酬,用来买书买肉打酱油,更多的是慰藉与浇灌自己时常焦虑、空虚、枯萎的心田。
这些年,眼袋泛起的柳也很少看我写作与发表的文字了。有天她对我说:“过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吧,好好打发我们余生的时间吧。”我点头同意。毕竟,一个长期冥想世界的人,如果不能敏捷地翻转腾挪到现实的铁打的生活面前,那将是虚弱的、没底气的、画饼充饥的。我那些来自于灵魂深处寂寞碾磨的文字,它只在内心的土壤里默默开花。
前不久的一天,我在单位收到了一封快递送来的信件。拆开,是熟悉的字体。信是当年那女孩写来的,她生活的那个县城,已经撤县设市了。在信里,她告诉我,她一直关注着、追随着我发表在各地报刊的文章,常常在网络上搜索我发表的文字。她说,依然很喜欢,并说我的文字有中年季节里的霜气了。她对我文字的评价,我特别认同。
我来到老街河流上的老桥,抬头望天,天蓝如眼瞳。我恍惚中感到,在这浩大的天地之间,有一双眼睛在空中一直默默凝视着我。在这人间,我不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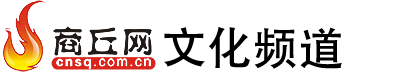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