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伟
母亲对我说:“燕子妈去世了,她都没回来,唉!”我“哦”了一声,不由回忆起那个眼睛里总是闪着光的玩伴,那个曾经邀天上明月的女孩——燕子。
燕子是我的邻居,比我大五岁,但我们俩能玩到一起。她带着我满村子跑,有时候还跑到村口对着茫茫远方大声喊话,恨不得能长出一双翅膀。向往远方,大概是人的天性吧。
孩子心疯,跑了一整天,晚上也不闲着,燕子拉着我在胡同里跑来跑去。小时候,快乐很简单。月色朗朗,燕子突然抬头冲着夜空的一轮满月大声喊起来:“月亮,你怎么那么大那么亮?你陪我们一起玩好吗?”接着她又唱起来:“月亮走我也走……”我看着燕子对月高歌,觉得她像发魔怔。
回到家,我跟母亲说起燕子与月亮的“交流”。母亲淡淡地说:“眼里有月亮的小孩,心比天大。”
六年之后,燕子考上了大学,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的父母兴奋得恨不得昭告天下,她家接连几天大摆宴席。邻居们都说,将来燕子要接父母去大城市,住大楼房,天天吃香喝辣。燕子父母每次听了这样的话,都笑得合不拢嘴。我很纳闷,同样的话我都听过一百遍了,可她的父母每次都像第一遍听到一样,保持着丝毫不减的亢奋。
燕子上大学前的晚上,我和她坐在她家院子里,面前的茶杯里有凉白开。她忽然端起杯子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然后她又冲我笑起来:“哈哈,还有一个你呢!”月光泛在杯子中,光影晃呀晃的。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股“出国潮”。我做梦也没想到,出国潮会与我们这个乡村产生联系。燕子回家后,对我说:“我想出国。”那时候,流行一个“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听了燕子的话,脱口而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燕子笑了,仰望着夜空说:“我就是想看看外国的月亮到底是不是比中国圆。”
“到时候你就看不到中国的月亮了。”“没关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听说有时差,外国的月亮跟中国的月亮不会同时升起来。而且,月是故乡明。”“没关系,外国的月亮也是升了落,落了升,哪里的月亮都一样。”一场关于月亮的讨论,像夜色中的密语,带着幽深的色彩。
燕子终于如愿出国了。后面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了。这些年里,我没有跟燕子联系过,她的家人跟她联系也极少。她的父母没能被接到大城市“住大楼房”,他们到死都守在乡村。听说燕子在国外过得一般。那时候有个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总想到燕子。
至今我都没有燕子的消息,她一直未曾回来过。父母去世,她都没回来,难怪我母亲要“唉”一声。燕子像一粒尘埃,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流落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在那里,她依旧是渺小的尘埃。
我总想,如果燕子不离开,她的人生有一百种可能,生活也可能有一百种轨迹。她工作,生活,在父母面前尽孝,做普通人该做的事。而如今,她在另一方天地里喜怒哀乐着。喜怒哀乐的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感受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天空,都只有一小片,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
人的一生有一百种可能,唯有月亮,亘古不变,永远是最初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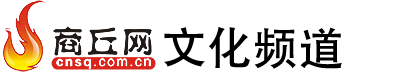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