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法力
出小区,沿着一条新铺的红蓝砖石的河边小路往东走,芦苇,野鸭,戴胜鸟,紫薇;绿风,花香,鸟鸣。一路心情生花,很快就到了一座小桥。
小桥也是新修的,拱形,彩虹似的。每天早晨七点前,桥南、北两头,路两边规规矩矩摆满了三轮车、四轮车,车上装满新鲜的蔬果。
那是一个喧闹的菜市场,小小的,热腾腾的。
夏天的早晨,乡下赶来的菜农,男女老少,脸上挂着露珠般清新的汗珠。瓜果蔬菜价格极便宜,品相虽拙朴,却新鲜得滴水挂露,像未经雕琢的村姑,袒露着泥土与草根香。
小雨纤纤,风细细。周末,晨跑后,我一身黑蓝色运动衣裤,在菜摊前晃荡。提一把俗绿的芹菜,拎几颗鲜红的番茄,准备回家。快七点了,管理人员该来清理市场了。因为这是一条上班上学的大路,不能造成交通阻塞。人群起了躁动,菜农与买菜的,似乎都不那么淡定了。
雨脚,似乎细密了些,凌乱了些。卖黄瓜的老人把塑料布上剩下的黄瓜吃力地往破旧三轮车上搬,身子佝偻成伶仃的虾。凉雨使他剧烈地咳,他似乎有些跛,行动很艰难。
“大爷,黄瓜多少钱斤?”问话的小伙子嘴里嚼着肉盒,趿拉着凉拖鞋,穿草绿色的大裤衩。他竟然赤裸着上身,细雨在他健康的肤色上凝成了碎珠。人潦草随意,像桥边坡上的一棵野树。
他走过我身边,带来一股浓浓的肉盒香,大大咧咧冲我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说一声:“对不起。”原来,冒冒失失的他,刚刚把我撞了个趔趄。
我想怒,蓦地,被他一头乱蓬蓬浓密的黑发触动了心底柔软的情愫:多年轻的生命!青春就是欢实与莽撞嘛!我轻轻笑了一下,心里原谅了他。
他把最后一片油腻腻的肉盒塞进嘴里,肥厚的手掌抹拉一把嘴,一屁股蹲在老人面前,故意大声喊着问:“大爷!哦,不,爷爷!黄瓜多少钱斤?”
老人见来了顾客,黝黑干巴的一张脸顿时笑成了金丝菊:“不贵,不贵,小(豫东方言:对年轻人的称呼)!要完罢?给你便宜!”
雨线密集起来,菜农们惶惶撤退,菜市场起了喧哗与拥挤。我被绊在了人流里,不得不在卖黄瓜老人破旧的三轮车前停留下来。
“多少钱?爷爷。”蹲在地上的小伙,胡拉着脸上的汗珠与雨珠,大声喊。
“十块罢。小!你都拿去。”雨声里,老人也用力大声喊。
小伙把地上的黄瓜划拉成一堆,又伸头往车厢里看,喊一句:“这几根,也归我罢!”
“拿去!拿去呃!”老人咳嗽着,颤巍巍地把黄瓜拿下来,放到地上塑料布的那一堆里去。
小伙从屁股兜里摸出一张五十元的纸币,皱巴巴,油腻腻,抬手递给老人。
老人突然慈祥地笑了:“小!不假罢?别坑我老汉!我也找不开呃!兜里都是碎毛克子。”
小伙涨红了脸,想发作,顿一顿,挠一挠乱蓬蓬的黑发,忍住了,嘟囔着说:“唉!不识好歹的老头,想做件好事,竟然还被怀疑了。”
小伙用湿漉漉的塑料布把地上一堆弯曲的黄瓜裹巴裹巴抱在怀里,立起青春壮实的身子,探过头去,在老人耳边大声说:“爷爷,回去吧!雨下大了。骗你是小狗!钱拿去,不用找了,我是对面肉盒铺子的。”
小伙回头指着路对面的一排早点铺给老人看,继续大声说:“本来,我想来给店里买粉条嘞,看见你……嗨嗨……如果是假钱,你尽管拿来找我!砸我铺子都没话说……”
小伙抱着黄瓜走了,背影活泼又俏皮,欢脱得像小孩子。
老人望着他的背影,举着五十元钞票的手哆嗦着,嘴唇一直嗫嚅着,沟沟壑壑的脸上布满水珠,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把菜放在路边的青草地上,从后面把老人低头蹬着的三轮车悄悄推上了桥坡。
一霎时,人散了,如潮水般退去,小桥恢复安静,只有温柔的雨丝又轻又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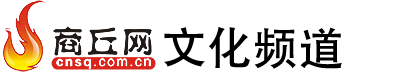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