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微雨,清凉,我揣了一把在人世跋涉时杂生的棱角,想念母亲,想念她的黧黑面容、斑白发色、粗糙手掌。
千般抵抗瞬时废除,跌宕心情瓦解,我在她的影像里走向平和。
母亲在二十岁时穿了花卡其布衫,及腰的麻花辫上仔细地打了根红头绳,额头乳发被汗水沾湿,脸膛红润欲滴,羞涩不已地走向父亲。
她站在这个清俊男子面前,内心忐忑如鹿冲撞,内里悄然生出绯红云朵,期许花落、蒂熟,一切行云流水,水到渠成。
云彩落地,即成烟尘。
和历来女子一般披了盖头,着了绣鞋,染上唇色和青涩时光一起盛大告别。然后,走入土坯房里,脱了一身大红喜色,捡起蓝边碗,架起敷着锅烟灰的陶罐,把身后日子和着灶火一起无奈而茂盛燃烧。
她咔嚓一声剪去长发,连着虚幻念想。脑后挽髻,走入水田,抓起谷粒撒入新翻秧地。
遇水而安,择水而居,临水而葬。于她,非旖旎佳话,只成就一生的劳苦宿命。
春日栽秧,夏日匀禾,秋日割稻,冬日晒谷。
她戴了草笠,卷了裤腿,深弓着腰背在日毒如火时劳作,双眼发黑任手臂机械挥动。几只肥黑蠕动的蚂蟥盘踞在她的腿肚上。村落里浮起一片零星灯火时,她走上岸来,抖落血已吸得饱实的蚂蟥,脱下泥点密布的衣衫,将自己浸在清凉河水里。
水声蜿蜒远去,蛙鸣空旷茫然,和着她无力的一声轻吁。
她在秋日里分娩。小儿撕扯着她的肉体,她在地狱里来回几度,终听得一串清亮哭声。她睁开疲软的眼睛,看到那一团粉皱皱的肉体,内心里涌上花好月圆。她流下泪来。
从此,更加无欲无求,将厚茧一再磨厚、磨厚。
母亲拖着疲惫在夜色里回到家,远远看到屋子里那盏亮起的油灯,大儿子已经熬好大米,小儿子正颠着簸箕收谷。她内心忽然饱实地温暖了一下,轻轻笑了。
她夹起钵里的猪肉,小心咬去肥肉,留下瘦的递到我们碗里,哪怕只是肉筋。她说:“肥的好吃!”她黧色的脸颊渐渐凹陷,如凭空生出的大渊,却不自知自省。
年节里偶尔扯上三五尺花布,她忘记了自己的衣服仅能遮体,补丁盖着补丁。她担心孩子们衣裳不整在学校受人耻笑。她说:“我老了,不用穿那么好看!”她难道看不见?她的棉衣已经百纳千结,不见底布的颜色?
冬日大雪,她行了几十里山路,挣扎着走去儿子所在的学校,送一双昨夜点灯纳好的棉鞋。她看着儿子穿上,顶着一头落雪欢喜地说:“晚上看书,你就不会冻脚了!”她忘记了自己手脚上的冻疮早已溃烂流脓,忘记了自己刚刚大病初愈,忘记了回家后仍然要在冬夜里赤手到冰水中去洗菜淘米捶衣裳。
在暗夜里听着孩子们的呼吸声,她夜深不眠,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缝书包、纳鞋底。最近,她的左眼渐生白翳,她只觉是小事,说右眼不是还能看见吗?至今都未就过医。她的耳朵亦渐渐不再敏锐,却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孩子们回家的声音。当我们在前面的田埂上叫一声“妈”,她便立时兴高采烈地从屋子里出来,迈过门槛站在院里,看着我们慢慢走近,笑着端上一碗汤。
她一生为物质绞尽脑汁,亦被许多忧心杂事纠缠。父亲外形一直英俊倜傥,她偏偏又是敏感如斯的女人,自然有许多争吵。她无人哭诉,渐渐哀怨。儿子的生活与感情也让她日日操心。她总是怕我们过得不够好,患得患失,不得停息。
母亲像一把巨大的纱网,将人世重而沉的苦痛全部滤去,只留下一个轻喜现世与我们。而我们不知世事的长大,不晓不懂不解其背里辛酸劳苦,在母亲撑起的暖色氛围欢喜雀跃;看不见太多的阴冷、贫穷、苦痛,只一味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甚至在不快时,生出某些怨恨。
在年少轻狂的时节里,觉得母亲的啰嗦唠叨让人厌烦,总是皱了眉忍受她的言语。认为所有的母亲都该是温文尔雅、娴良淑德,于是对她的执着而心生埋怨。与之顶嘴,甚至竭尽所能地伤害。
然而,母亲终究是忘却了这些我们给过的伤害。她要的花好月圆,只是我们的平安。
母亲在孩子们日渐蹿高的时间里生了许多白发,身体渐衰。早年里因为劳作,以及与父亲争吵而落下的病痛折磨起她来。她独自找些土方子疗养,从不告知我们她的疾病,怕我们牵念。
偶尔归去,便见她的身形越发佝偻了,头上已是一簇簇明亮的雪花。有一天我翻看她的头发,发现头顶竟已经是一片雪白。我瞬间感到巨大而尖锐的悲哀。我的母亲,她竟这样快地老了,还来不及享半点福分。她终日皱眉抵御那些积攒的苦楚,我们心生不忍。欲好颜好色地服侍,她却不依,只说自己是好的,不必虑。
她偶尔打来电话:“想家了吗?”便有浓浓的情愫生出来,知道母亲又在挂念。于是微笑起来,告诉她我们都好,万事顺心,不要挂虑,只需好生照顾自己。挂了电话坐下来,把那个倚在门上守望的身影揉进一团茶叶,和沸热的水一起,缓缓喝下去,暖了心肠,暖了前生末世的念想。
母亲,不管走得多远,我一回头,便能看到你的目光。那个旧日堂前的身影,在我的生命里深深嵌入,冥顽不化。
年关时围炉夜话,母亲把厨房收拾妥当,与我们唠嗑。她说:我这辈子,就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过得好好的,我就安心了,就行了。
我们久久无言,眼睛微湿。她要的,只是我们的幸福。于她,便是最大的圆满。
烛,耗尽自身,积攒光明,映他物他事。
而母亲,亦如烛。她默默完成一场生命的传承,然后,就退到时光背后,默默无声。只在夕阳里翻看旧相册,来证明她匆匆而辛苦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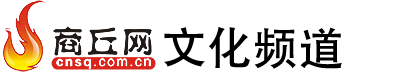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