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中这样写:“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读到“坐席”二字,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我的童年在小镇老街度过。当时家里虽不愁吃穿,但肚里油水却不足。一年中除过年之外,就靠跟着大人们坐席打打牙祭。
街坊邻居不论红白喜事,都会摆酒席,俗称“做事”。主家提前一两天在家门前搭棚支锅,请镇上有名的厨子掌勺,杀鸡宰鸭,炖肉炸鱼,左邻右舍出人出力,借桌借凳……主家还会请来一位总指挥,小镇人称“支客司”。这人通常在街上或族里有一定威望,对婚丧嫁娶流程轻车熟路。他会根据主家“做事”的规模大小,按各自的特长派活,并用大红纸张贴公布。
坐席,可不是白吃,要随礼。主家会委托两个帮忙的人,在门前支一张桌子,一个人记账,一个人收礼。谁随了多少礼,一笔笔写得很清楚。那时普通礼金通常两三块钱。也有五块十块的,多是自家亲戚。送得多的,通常去一家人。
我那时特别喜欢坐席,见别人家门口摆起大桌子就垂涎三尺。小学三年级时,同学小红的爸爸车祸去世,她家门前摆了好多桌酒席。我那时年少不懂事,一脸羡慕地对戴着黑纱的小红说:“你家吃得真好啊!”这话被小红的妈妈听见了,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妈听说后,将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婚宴。小镇男方娶媳妇,哪怕家境不富有,也要打肿脸充胖子把婚事办得体体面面。结婚的头天晚上,男方家也会摆席。听大人说那叫前席,主要招待一些亲朋好友,外加一些为婚事帮忙的人。我妈是热心人,哪家街坊办席,她都主动去帮忙,我也跟着一起去大饱口福。
婚礼当天中午的酒宴叫正席。开席的时间通常在12点。已随过礼的客人一见碗筷摆好,赶紧蜂拥而上,争着抢占座位。不过有两桌不能随便坐,那是为送亲客(新娘的娘家人)准备的席桌。
一碗碗,一盘盘,鸡鸭鱼肉摆满桌,煎的炒的蒸的煮的,应有尽有,芳香四溢,色香味俱佳。席间,主家一直吹吹打打,鼓乐齐鸣,不时有小孩子高叫“新媳妇来了”。随后鞭炮响起。吃席的街坊们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转过头看热闹。
第一桌接近尾声,客人还没离开座位,下一拨等着坐席的客人便涌了进来,全然不顾桌上还一片狼藉。听小伙伴英说,她小叔有一次吃席感觉不过瘾,趁没人注意,又跟着第二轮吃了一顿。
1988年,我小舅结婚,外婆家杀了一头猪,我连续几天大鱼大肉。在那次酒席上,我生平第一次吃到夹沙肉,那滋味到现在还回味无穷。远嫁福州的小姨也专门赶回来,送了五十元礼金,这在当时算是厚礼。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坐席,是隔壁权叔娶媳妇。那年腊月的一天,权叔的母亲一大早敲开我家的门,进屋就焦急地求我妈帮忙。权叔原定腊月二十四结婚,眼看婚期临近,女方突然悔婚,说是嫌她家兄弟姐妹多,家境贫穷。母亲不知想了啥招数,当天就带了些烟酒糖去了女方家。几天后,权叔的婚礼如期举行。
我妈按规矩送了三元的礼金。权叔的父亲却专门来我家隆重邀请去坐席,特别强调是请一家人,这在当时算是最高规格。因我妈是她家的功臣,我理直气壮地去吃了好几顿。席上的凉拌猪蹄那叫一个美味,还有香糯的扣肉,闪着明晃晃的油花。
那年头坐席也闹过一些笑话。有一年我姑父的母亲去世,过了一个月,他还戴着黑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有一天傍晚,他从一家办丧事的门前经过。那家的“支客司”见到他手臂上的黑纱,不由分说将他拉到酒席上。还有一次,表婶家亲戚的孩子做满月酒,表婶没空去,就让她上中学的女儿去随礼。那天街上好几家办席的,表婶的女儿不认识主家,吃完酒席后才发现拜错了码头。这事到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还觉得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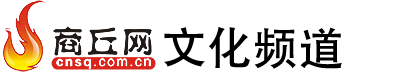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