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元
一根甘蔗,把腊月的香甜搅动起来。
午饭的时候,伙食团的阿姨切了一盘甘蔗出来,小巧精致,圆润光泽,用嘴一咬,那混合着时光的甜香立即像潮水一般涌上心间。
乡间有谚:红萝卜,蜜蜜甜,看着看着就过年。而在我的心头,腊月还有甘蔗,像红萝卜一样,都是新年快到的前奏。
小时候老家屋后有一溜狭窄的自留地。爸妈在周围种上了一圈橘子树。自留地里,随着季节的变换,他们把西红柿、茄子、辣椒、四季豆、豇豆、蒜苗、韭菜……一个个铺排得井然有序。在偏西的一个角落,他们也为甘蔗留下了一方出头之地。
从春天到秋天,我幼稚的目光是看不见那一片甘蔗林的,我的心思,停留在嫩嫩绿绿的瓜果蔬菜之上。我不靠近它,它实在普通得像我一样。而后它挺拔起来,却有着如剑般锋利的叶片。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还要在身上留着时光的“节”点。
但冬天不同,甘蔗经过漫长的酝酿,终于成熟。成熟的甘蔗在腊月间的乡场里,成为迎接新年当仁不让的主角。一根根甘蔗被人高高低低地竖起来,远远看去,就像一顶顶褐色的帐篷。卖甘蔗的手持砍刀,对着围观的人说:“来来来,你们用刀削到哪里,我就砍到哪里,不甜不要钱。”
这话充满诱惑。有人拿着砍刀,站在甘蔗前,将甘蔗端端正正地竖立,然后屏住呼吸,趁甘蔗将倒未倒之际,一刀劈将下去。
这是一个技术活,劈得太靠外,甘蔗的皮削不了多长;劈得太靠里,容易砍空;只有分寸刚好,才能把甘蔗皮削得够长,才能得到一截长长的甘蔗,从而在他人艳羡的目光中离开。
现在想来,这自然是卖甘蔗的一种推销手段。但小时候我也乐在其中,时常想去挑战。当然这时的甘蔗,也愿意为人们的欢乐无私奉献。
我曾问父亲,甘蔗为什么那么甜,父亲说甘蔗的甜来之不易,和人一样,都需要漫长的磨砺。我问父亲甘蔗为什么有节,父亲说它进退有节清风亮节。
父亲是老师,喜欢讲道理,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那些话让我似懂非懂。我更“讨厌”他一到腊月,就命令我把橱柜的碗全部拿出来,背到山坡用泡石“沙碗”。如果碗不锃亮便返工,就要被他吼。还让我和他一起磨豆腐……我在无聊重复的脚步中天旋地转,他在一旁竟然鼓励我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直到父亲说“推完磨,我给你砍甘蔗”,我的精气神才一下子满血归来。是甘蔗的甜,让我燃起期盼。
很多年后我做了父亲,也懂了父亲。我知道父亲想拿甘蔗说事,让我能有一个节节攀高而平安幸福的人生。只是父亲不知道,因为甘蔗,好多人的命运被阴差阳错地改变。
它们的故土在太平洋群岛,后来通过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印度和欧洲。在没有甘蔗之前,欧洲人只能通过蜂蜜获取甜味。甜是人类乐此不疲的追求,当欧洲人第一次见到甘蔗的时候,禁不住为这种作物疯狂起来。但甘蔗种起来耗时耗力,想大批量种植在欧洲显然不行。欧洲的殖民者于是就把目光放在了美洲,在拉丁美洲建了很多甘蔗园。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他们从非洲贩卖黑奴……一根甘蔗,就这样搅动了整个欧洲,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
这样的说法让甘蔗背了锅,真相是一切源自人性中一种叫贪婪的东西。但历史有时真很神奇,造成改变的,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物件。
时光荏苒,那些旧时的甘蔗田在城市的喧嚣中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而我家老屋背后的园子,也早已荒芜。
然而甘蔗的甜美并未消失。当新年的阳光与甜润的甘蔗相遇,一场关于时光与味觉的盛宴还是悄然而至。我总觉得它像一个外表粗粝内心柔软的老友,在春节快到时返乡归来,喜欢把一年的酸甜苦辣对我倾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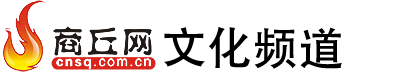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