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民
“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经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这是维特根斯坦的名言。
值得注意的是,过了三十年,“我们”还健在,但有些“语言”已经溜走。
日前,偶然翻到当年的博客,看到自己在《大河报》写《荧屏沙龙》专栏之际的文字,恍如隔世。例如讽刺彼时“广告满天飞”的荧屏,笔者借阿Q“非礼”吴妈为切入点,分析了五点“作案原因”:一是那天他喝了二两黄酒,“酒叫人想家”。二是他对吴妈的追求“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临杀头还在追求,“一直在努力”。三是他的眼里只有吴妈,提前半个多世纪唱出了“让我一次爱个够”。四是从“女权”角度来考察,“做女人,挺好嘛”,不必委屈自己。五是说明“男人更需要关怀”,尤其是于“悠悠岁月久”之际在野外“东奔西走”的男人——试问,哪一位还能够准确地说出广告语卖的是什么物品?
语言有相当的稳定性,世界变化快不快,语言的“进步”速度当为晴雨表。
1.语言是存在的家,只要见到某些语句,就不难从“情绪记忆”转化为有图像的“形象思维”——1978年,吾侪踏入大学门,唱的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都以为“二十年”遥远如往事,早得很呢。不料一眨眼两个二十年过去了,语言变成了“曾经存在的家”。
2.“单位路由器坏了,有人在小黑板上写道:‘陆游气坏了!’过一会,下面多出一行字,‘那就找欧阳修!’又过了一会,有人写:‘欧阳要是修不好,那就找王之换!’再过了一会又有人写:‘王之换不了,找蔡元赔。’……”遂记起2016年的网络用语“蓝瘦香菇”即“难受想哭”的谐音。为什么这“谐音梗”长盛不衰?
这不是进步,而是不读中外名著而语言贫乏的表现之一。
3.“如果你的辅导员掉进了水里,那你的专业能干些什么?”经济学系同学:“当然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拉他一把。”服装设计系:“把这悲伤的记忆做到下一季的灵感板里面。”新闻系(帮学校辟谣):“我们并没有这个辅导员。”人力资源管理系:“紧急招聘人来捞他吧!”……
问题在于,谁想到的“辅导员掉进水里”这个命题。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如果”。
4.“勤能养财,学能养识,善能养福,乐能养寿,动能养身,静能养心。”
请问什么东西能够“养”一个民族的语言?
5.哥伦布说,巴哈马岛上“有利于健康的大河交织,有的树在开花,有的树在结果”。这不仅是语言的张力,同样是文字的魅力。类乎唐诗里的“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6.五四新文学革命,陈独秀声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没有古文的基础,他的生动准确的概括从何而来?
7.“照逻辑讲,吃了感冒丹导致感冒;吞了伤风丸会引起伤风。其实不然。不能看字面。‘感冒丹’跟‘伤风丸’,是‘压缩’了的词语,应当理解为‘预防感冒丹’‘防治伤风丸’。”——2008年年底,首次见到陈原先生的小册子《在语词的密林里》,爱不释手,这才明白“社会语言学”的魅力。
8.郭沫若用“年青的女郎”写“眷恋祖国的情绪”,而海子写祖国却是命名为“以梦为马”——骑上了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前者怎么看还是热恋美女的身姿,后者才是现代格局与表达。
9.海子评论荷尔德林:“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他说收获季节“麦浪和月光/洗着快镰刀”,他用砍过的与洗过的词汇表达“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
10.或曰,翻译中的女名,如“苔丝”,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因为读者“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鲁迅说“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譬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儿叫作Elizabeth Tolstoi,全译出来太麻烦,用‘妥奶丝苔’就明白简单得多。但假如托尔斯泰还有两个女儿,叫做Mary Tolstoi et Hilda Tolstoi,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字样,反而麻烦得多了。”
语言也有自己的界限,无论中与外,简与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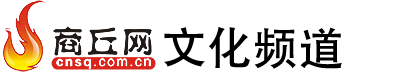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