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学习任务比以前加重了,学校给我们增加了夜自习,让学生自备油灯。娘从集上给我买回一只用铁汁铸造的油灯,碗状、平底,这边有把可用手端,那边有豁可放灯捻,添上棉油,点着灯捻,灯就亮了。这在我家乡一带叫作棉油灯,农民家庭多用这种灯。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同学们用的油灯也分几种:经济条件差的多用棉油灯(灯和油都贱),经济条件稍好的多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墨水瓶虽然好找,灯芯也好制,但煤油比棉油贵得多),经济条件再好些的多用带罩的煤油灯(灯和煤油都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生活好转了,几乎所有同学都换上了带罩的煤油灯。这种煤油灯由灯罩、灯头、灯芯和灯座组成。灯罩容易污染变黑,需要及时擦拭:灯罩两头细,中间鼓,一头用手捂严,一头用嘴往罩里哈气,用块软布缠在手上,伸向罩壁,仔细擦拭,直至灯罩无一污痕,光洁无比。然后将灯点着,灯头先拧小一点,等灯罩发热了,灯头再拧大一点。这时,光焰顶部出现青蓝色,跟炉火纯青差不多。一个教室里,许多煤油灯散发出许多光晕,许多光晕会合起来,大放光明,便将室内桌椅黑板门窗梁檩照得很亮。
宋朝诗人陆游曾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写道: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他在41岁那年秋夜读书时兴味浓烈,仍然保持着少年奋发勤读的精神。而我们这班学生,在这光线柔和、朴实无华的环境里,同样学习知识,增长本领:有的温习当天新学的功课,加深理解,巩固记忆;有的重做做错的作业,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有的预习明天将要讲授的新课,把不懂部分事先圈住,以便老师讲新课时格外注意听讲,弄个真正明白;有的面向黑板,板书一串串数字,演算一道道难题;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私下里交流着学习心得与体会……
煤油灯从灯罩里飘出缕缕黑烟,钻进我们的鼻孔,鼻孔成了两个黑洞。我们只好停下手中活,掏出手绢,将黑洞擦净;煤油灯燃到一定时候,灯芯上会结出灯花来,不时发出爆响,我们只好摘下灯罩,剪去灯花……所有这些细节,是煤油灯故意给我们添麻烦吗?不是。我以为这不是添麻烦,而是给我们的学习有意安排的小插曲:它怕我们用功过度,损害身体,想让我们趁此机会松一松神经,歇一歇脑筋……
说起煤油灯来,我倒想起鲁迅先生在北京故居绿林书屋(也叫老虎尾巴)里夜间写作时常用的那盏高腿煤油灯。我在一篇拙作《绿林书屋造访记》中,曾经写道:
先生1924年5月26日,从西四砖塔胡同61号一位老乡家里搬进绿林书屋,1926年8月26日离开绿林书屋南下广州。在这两年零3个月的日子里,先生一直在那盏高腿煤油灯下坚持夜间写作。有时精疲力竭了,就放下笔,倒在床上和衣而卧,睡上两三个钟头,像战士在战壕里抱枪打个盹一样。醒来之后,抽支烟,喝杯茶,吃点零食,就又爬起格子来,结果写出200多篇作品。其中包括《野草》《华盖集》及其续编、《彷徨》《朝花夕拾》以及《坟》中部分作品,同时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热风》和译著《出了象牙之塔》等,用以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
我在沉思默想间,仿佛看到听到了先生在那盏高腿煤油灯下跟文学青年谈话时的音容笑貌:仪态万方,妙语连珠,谈对黑暗的憎恨,谈对光明的追求,谈韧性的战斗,谈文学创作,谈艺术修养……屋外冰天雪地,数九寒冬,屋内欢声笑语,春意融融……
还有一位名叫方敬的作家,曾在散文诗《灯》中这样写道:灯,是人类的老祖母,我们都是它的沐恩人。让我们大家都深深感激那盏在黑夜里燃烧得明亮的灯吧。是它用和平的光辉照彻了我们未成年的和成年的心灵……
在灯火似抛金撒银的今天,不论城里还是乡下,很少有人再点煤油灯了;就是点过煤油灯的人们,对煤油灯也许早已淡忘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煤油灯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却益发光彩照人,每逢忆起,倍感温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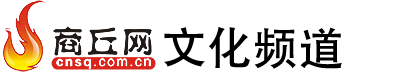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