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变得越来越瘦小了,就像一位日渐衰老的老人,失去了很多曾经的纯洁、欢乐和忧伤。村庄,也渐渐地远离了田野、庄稼、盐滩,以及柳燕的婉丽,布谷鸟的深沉,还有很多令人难以释怀的细节。
这个村庄,正被高楼和坚硬的混凝土路面一点点地塞满,犹如一个变了形状的口袋。再也见不到街头上那一排排合腰粗,身形却极度扭曲的,曾为村庄的无数个日夜哼唱过歌谣的老柳树了;再也见不到那几棵陪伴着村庄风风雨雨成长起来,曾被视为村庄灵魂的古槐了。
那些老树,曾经是如此真切地依偎过村庄,抑或是守护吧。那时候,连村庄里的大人们都对它们充满了敬畏。人们从不会有意地去伤害它们,任由它们肆意地生长,并一年一年地老去。对于春天的感觉,那些老柳树是最敏感的。当它们的枝条变柔、变绿的时候,村庄的泥土也开始变得柔软起来。
相对那些谦卑的庄稼人,老柳树们好像并不懂得含蓄。当它们坚决换绿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那些嫩黄的叶芽和柔绿的枝条,便将村庄的街头染上了大团大团的绿。一阵风或一场细雨,都会把那一团团的绿渲染得分外惹眼。
在乍冷乍暖的春天里,村庄里起早的总是那些老人。他们扛着一把铁锨,缓缓地走在沾满泥腥气息的雾霭里。他们或从村东走到村西,或走向那个通往田野的路口。然后蹲在麦田旁,点上一袋旱烟,与麦子说一说话。
其实,田野已经不需要他们做些什么。肩上的铁锨,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它更像是一根支撑他们行走在清晨里的拐杖。
那几棵替老人补足了觉的古槐,终于懒沓沓地醒来了。当它们还打着哈欠的时候,田野里的麦子已经开始酝酿着绣穗了。
麦田里,偶尔间隔着一块闲置了一冬的土地,也已经被翻耕成了微微的波浪形。那些被犁刃惊扰,并几乎被泥土湮没的野菜,仍固执地冒出来,并开出细小的花朵。它们的固执,犹如一个个将心扎在泥土里的农人。
耕牛从古槐树下往返经过,还有鸡们、鸭们,以及一群追来撵去的发情的狗。那些灵性的耕牛从古槐树下经过的时候,它们总会不由自主地驻足,仰望一下天空,或回顾一下身后。它们就像是在跟那些村庄的灵魂打一个招呼。在冥冥的世界里,一定还有很多令人无法琢磨的东西,但牛懂得。
蝉的鸣叫,与在古槐黝黑树皮上不停攀爬的蚂蚁,将村庄的夏季一点点地拉入秋季,直至它们神秘地隐失在透明的冬天里。
霜气,将落尽叶子的柳枝,凝成了老人的银须。那几棵枝头上仍零星挂着几个树荚的古槐,也默默地开始走进一个新的梦境。
那些曾在清晨扛着铁锨,从它们身旁不知道往返过多少次的老人们,仿佛也不忍心惊扰它们。他们慢慢地走过,轻声地咳嗽着,直到走出老远,才将嘴里的那口浓痰啐到地上。
街头的空旷,一直将村庄延伸到田野,又延伸到了盐滩。那些已经收敛了长势的麦苗,丝毫掩饰不住田野的空旷。远处,有一小片未刨掉的苞米秸,它们东倒西歪地站在那,与枯草融为一体。密密麻麻的麻雀栖在里面,静静地眺望着天空,偶尔的鸣叫,反而变得极为悠长。
盐滩上,那一丛丛望不到边的碱蓬,早已变得枯黄。偶尔,有几只沙云鸟略显惆怅地漫步其间,它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家。或许,盐滩上每一处角落都是它们的家。
将田野与盐滩衔接起来的,唯有艾草。它们的性情,像极了庄稼人,无论放在怎么偏远的地方,都能扎下根。在夏天的时候,它们曾经那么贪婪地生长着,端午节的镰刀,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们的长势。但在这个冬天,它们也懂得收敛,把所有的期望都埋在泥土里。
干枯的艾草,散发着淳朴的清香,溢满了村庄的周围。它们,就像是为这个村庄而生。
一位村庄的老人,扛着一张铁锨,蹒跚着朝那几棵古槐的方向走去。冬天的落日,并给不了它们多少温暖。但从他的脸上能够看出,他的内心此刻充满了感激。
他走到其中的一棵树跟前,拄着铁锨,用干瘪的手掌轻轻地摩挲着黝黑的树干。他什么也没有说,可眼睛里却好像对古槐诉说完了一辈子的心事,就像那些从树下经过的老牛。
又一个黄昏,村庄西头的十字路口上,慢慢地走来一群穿着白衣的庄稼人。他们齐齐地跪下,并点燃一对纸马。此时,他们谁也不许落泪,那是怕别离的眼泪打湿了老人的前程。每一位村庄的老人,都将从这里重新启程,投入到那个距离遥远的世界里。未来是喜是愁,并没有人知道。
或许,那些老者在跟古槐告别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古槐的诉说中获得了什么秘密,所以村庄的老人大都走得安详。
幽幽凄凄的唢呐声,响彻了村庄。野外,有一片艾草不知何时被人点燃。浓郁的艾草香伴着碎雪,缭绕在村庄的上空。它们是在尽力为村庄祈福,还是在用生命的气息充盈着日渐瘦小的村庄呢?
只是眼前,那个灵魂的出口,却越来越迷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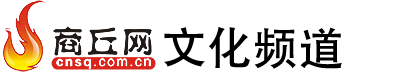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