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小区毗邻一块打围多年却迟迟没有开工的荒地,地就在我家生活阳台对面。在这块荒地上,各种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除隆冬,一年三季,接力不断。从立夏早玉米点下,到秋分晚玉米收获,布谷鸟的叫声一直是荒地中的独唱——大概只有一只。“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它叫得有些凄凉,有些旁若无人;七八只画眉鸟在密林里扑腾,翅膀扇出的风声四下流淌;麻雀最是闹腾,叽叽喳喳,呼啦啦站满一棵黄叶半落的树的所有枝丫。待不住,又惊乍乍飞离,在空中扯开一张灰的大网;蛐蛐儿金口一开,就仿佛被永动机控制了声带,金属的光芒颤颤闪烁;连蚊子也发出机群战斗时的嗡嗡声,攻击、驱逐我这个外来入侵者——这里是布谷鸟、画眉、麻雀、蚊子的领地,它们用声音昭示它们对这块荒地的主权。
有一天,挖掘机拖着隆隆的低吼来了,履带哐当哐当。附近种菜的人闻讯赶来,立即手忙脚乱抢收蔬菜。一片嘈杂的抢收声夹杂着钢铁机器霸气侧漏的轰隆声和鸟儿从荒地密林中弹出奔逃的啾啾声,声音的战场血光冲天。荒地被挖掘机的大铁螯刨了无数遍,又被运渣车的轮胎碾了无数遍。那夜,往日声音缤纷的荒地终于隐入尘烟,一片静默。
近些年,尽管我的睡眠质量一向不差,夜晚的我还是会被一声声炮响炸醒。送殡的车队,专门鸣炮开路的炮车,火化制度已推行了好几年,省城郊县的送殡的仪式却没有丝毫简化。电子炮砰砰,仿佛是亡灵离家上路,通往冥界途中最后的呐喊。我想起我过世已十余年的岳父。那年,岳父在省城医院做脑溢血手术,因为送医不及时,手术宣告失败。妻子的幺爸拿主意赶快把岳父往老家拉——按医院流程,如果岳父在医院落气,就由不得我们了,只能送到殡仪馆火化。岳父一动不动躺在老家的床上,四下死一般的静,只有氧气吸入器湿化瓶里的水汹涌翻滚,发出咕噜的声音。那声音被房间里的冷寂放大,似乎冷与热、黑与明、隐没与飞升正在进行一场拉锯。慢慢地,咕噜声渐趋于无,我感到那声音在沉沉下坠而岳父的身体却越来越飘,轻得如一片被幽风吹起的白羽。突然,一股闷气从他的鼻孔艰难涌出,像是一声沉入深渊的叹息……
楼下挖掘机进场后,我每天都忧戚地从我家阳台望过去——光秃秃的荒地已覆盖上了防尘网,像是施工者施舍给褴褛大地的最廉价的遮羞布。那块荒地被四条柏油路环绕,一辆辆汽车正在加速冲锋,汽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像是流动的水,直朝我耳朵里涌。从那以后,我开始失眠,开始纠结于各种声音应不应该在彼时彼地出现,我甚至拨打了市长热线,投诉噪音扰民。我的耳朵里似乎一直有声音在低频共振,我的眼睛有些恍惚。失去各种虫鸟声的抵挡与调和,那些声音流动成一个钢铁的、火焰的、水泥的漩涡,将我捶打又熔化,熔化又凝结。在荒地中央,几台打桩机正拼命工作,它们的哐哐声随同被它们驱离的那些虫鸟的声音,正沦陷于那个巨大的漩涡……
据说,这块荒地上将拔起一所公立小学,今年九月就将招生。已持续打桩好几天,因为抢工期,周末的清晨也不例外。坠落,曾经在这块荒地上鲜活多态存在的声音的坠落已成定局;升起,很快将有成百上千小学生活泼的声音从这里升起。一时间,我说不出我该为那些坠落悲伤,还是该为那些升起欣喜。
回头想想,这么多年来,我从单调寂静的乡村出发,来到炫彩、丰富、庞杂的城市,我以为我会陶醉于我追寻的声音世界。年近天命,我才明白自己的无知。可是,诸多“事后明白”,都必须用经历去验证才能深刻体会。这一遭,我走得并不荒唐。假如让我重来一次选择,我也依然只能背负父辈的和我的“脱下农皮”的梦想,飞蛾扑火般奔向眼前这个众声腾喧、万物鼎沸的城市。那粉身碎骨化为灰烬前的光明、盛大、温暖值得黑暗中的一只蛾为之无悔一跃。
常常怀疑,我新近出现的对城市种种声音的挑剔,是否如我曾经鄙夷的城市原住民一般矫情?在那些声音的背后,是多少个不得不靠制造并不悦耳的噪音方能赚得钢筋工钱、泥水匠钱、木工装修钱、货物运送钱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和我一样,我们有同样的出身,同样的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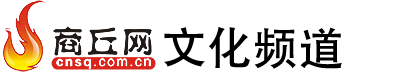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