皱巴巴的大地刚从冬的被窝里钻出来。光秃的黄土地上,尘絮在风中变换着形状。可有心人还是发现,几株绿草在一片枯叶间探出脑袋,枯叶下藏着点点嫩芽,大有铺天盖地为山河披上绿衣的架势。春天真的来了。
父亲在地埂上走着,很慢,很吃力,他那双受过伤的脚还没完全适应气候的变化。我毫不费力超过了他,回头看,他正对着一棵小树端详。他绕着树瞅了瞅,摇摇头,又往前走。
我不记得父亲看了多少棵树,他一直在摇头。我想,他不过是为打发无聊的时间吧。后来,他在一棵樱桃树前停下,右手捋捋胡子,嘴角勾勒出一丝微笑。他蹲下去,从下往上轻轻摸了摸树干,跟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
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为什么父亲把它当宝贝呢?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百思不解。父亲搂着树,小心地把树干一点点往地上压,待树尖伏在地,又搬一块大石头压住。他在旁边静静地守了一会,看到石头和小树没什么动静,才起身离开。
“它会死吗?”我有些担心地问。
“从小不捂,到大不弯。”父亲看着我说。他表情严肃,嘴唇紧抿,仿佛心里装了一块秤砣。
我坐在学校的课堂上,跟着老师念:树不弯易折,人不弯常败。这跟父亲压弯的小树有什么关系呢?我看看老师,他慢悠悠踱着步子。我的疑惑始终无从解答,很多次,我绕道去看那棵樱桃树,它像一截被随意丢弃的废柴。
尽管在泥土里成长,我却从未参与庄稼的播种、生长和收割。我只知道,是父亲披星戴月在土地里刨食,是苞谷、洋芋喂饱了我们干瘪的肚子。我整天埋在书里,不再试图寻找樱桃树被压弯的答案。事实上,我渐渐忘记了那棵树,我的生活早已被书本和考分填满。
当然,对父亲而言,没有什么事情大得过土地。那天,我跑回家,父亲正坐在一堆凌乱的木头中间。我一眼看到了那棵樱桃树,它变得粗壮,弯的弧度也那么自然。父亲像有魔法似的,樱桃树在他手里一点点变得溜滑。接着,他又鼓捣起木头,斧头敲击凿子在木头上发出沉闷的哼声。他用力一吹,木屑飞起来,出现一个长方形凹槽。一块块木头像列队整齐的士兵,臣服于父亲灵巧的手。
“又要春耕了。”父亲一边说,一边把那些木头拼接起来。我看到他手上青筋凸起,似乎用了很大的力。随后他靠着墙坐下,双腿夹着即将成型的犁,用斧头在木头连接处轻轻敲打。我知道,一张好犁,不仅仅是父亲的宝贝,对于土地、耕牛也尤为重要。
我突然有些理解父亲,那双压弯樱桃树的手,甚至是聚全身力量压弯土地的手,同时也把一个家庭的命运捧起来。它早已形成一股巨大的暗流,淌进我幼小的生命里。
可是关于父亲,我又真正理解多少?他在我们身上花的心血,不比在土地上少。儿女们像地里的苞谷、洋芋,长势好坏,决定着他一年的心情。他送我们读书、识字,用血肉之手托起我们的远方,逃离土地,这夹杂着多少决绝和不舍?
“要读书,读出个样子来。”父亲说,“不能让子孙后代一辈子当泥腿子。”那年,姐姐收拾行李书本跑回家,要去昆明打工。父亲抄起一截细竹棍,含着泪一步步把她撵到学校。而我,在父亲冷峻的眼神里,从来不敢放下书本。
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父亲的坚持,我们会不会还在山里啃食泥土。大浪淘沙,我们是故乡最幸运的那粒泥土。那么,即使负重的脊梁如樱桃树那样弯曲,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没有完全长成父亲期待的样子,但我们血液里流着他的韧性,于曲折中负重前行,不敢有丝毫懈怠。从一座山到一座城,我们是泥土里的种子,根足够深,信念足够坚定,熬过漫漫长夜终会发芽。
退回时光之河,我看到春天里的父亲,他跪向大山,用一辈子守护土地的诚实、犁头的靠谱、季节的守信。他告诉我,我们用双手耕耘岁月,用血汗浇灌的生活之花,是任何人也偷不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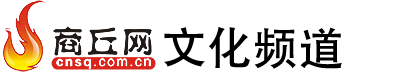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