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盈旭
清新湿润的早晨,蜀葵花开得好早,坐在五月的风里,红裙子也抻不稳,像高个子的女孩,裙摆飘起,按不住,手忙脚乱红了脸。
早饭后,父亲在日光花影里给老黄牛套上了石磙,准备去打麦场。他粗糙的大手掌拨棱了一下肥厚披垂的大牛耳,对老黄牛说:“老伙计,酒足饭饱了吗?咱还得去打麦场,再打磨打磨?省得别人笑话咱,说什么场不光油牲口懒。”父亲口气温和,像对兄长说话。
母亲给父亲备好了打场三件套:大肚子瓷缸的黄汤老茶、小马扎、草帽。娇小的母亲安静地站在门边,只等父亲絮叨完,随时跟着出发。
父亲一回头,看见母亲温顺恬静的模样,笑一笑,顺手拽下一朵蜀葵花要给母亲戴头上。母亲往后躲,嘴里说:“别闹了,多大年纪喽?还戴花,别人要笑掉大牙呢!”
高大的父亲兀自一手揽住娇小的母亲,一手把花戴在母亲黑溜溜的发髻上:“谁笑话?杨三姐永远是小姑娘嘛,十五十六正当春呢!”
母亲红着脸,抬手轻轻摸了摸头上的花朵,把颤颤的它又簪稳了。蜀葵花明亮亮地红艳着,安稳,暖贴,甜蜜,像母亲的一颗心。
高出了母亲小半头的蜀葵,正努力把一朵朵花举进阳光,像给母亲撑开一柄柄花伞,灼灼得不像话。
牵着老黄牛,父亲沿着门前的小土路往打麦场走。小路上,野花野草听风听雨,见缝插针,实在把生命抓得紧,它们肥硕冒油的模样,只能让人吐出俩字:蓬勃,像小村彼时的气象。
其实早在春天,父亲的打麦场就打磨好了。春天时,大黄牛拖着石磙一遍遍压。吱吱呀呀,从杏花白到桃花红。父亲是个极精细的人,农桑事也做到极致完美,打麦场被他打磨得像一面瓷实光滑的镜子,又像一张包浆了的席子。可是,经过一个春天光阴的路过,打麦场边边角角长起了细细碎碎的野花野草,像十七八岁小伙嘴上的嫩胡茬。父亲不能容忍,隔三差五就带着母亲去铲除,毫不留情。铲了发,发了铲。
打麦场的边边角角被父亲修理干净了,可场中央呢?它禁不起几场春雨与阳光湿湿干干地揉搓,从少女光洁瓷实的脸蛋变成了老妪的一张脸,起了皮,起了褶。
父亲岂能容忍!于是,喝过清新麦仁汤的几日后,父亲又拉着老黄牛,套了石磙,再一次去打磨场地了。近乎要求完美的他是不能容忍尚未使用的场地满脸褶子的,一如他对母亲。在他眼中,母亲永远十五十六正当春,不能老去,怎可老去?
风自垄上来,带着苍黄的颜色。不远处,麦子马上就要成熟了。也许一夜热风吹,次日,大田里黄澄澄的麦子波浪似的溅出来了,谁能抱得住?
丰收在望。父亲黄黑的脸上露出虔诚的笑意。
打麦场收拾好了,他坐在小马扎上喝茶、抽烟。老黄牛不停摆着尾巴,一只俏皮的白蝴蝶停在牛背上,怎么也轰不走。
有邻人走过来,顶着大草帽,黝黑的脖颈间闪着亮亮的汗水,父亲起身招呼着。来人摘了草帽,一手卸下肩上的锄头,一手接过父亲递来的烟卷。两个男人低头圈火,父亲甩熄了一根细细的火柴,丢在脚下,踏上去,用脚尖捻了。
“朱先生,你家的打麦场忒光溜,苍蝇站上去都打闪,像大姑娘上花轿刚绞的脸。”邻人由衷地夸赞父亲。
父亲吐出一个闲淡的烟圈,笑了笑,拿眼角去寻母亲。一旁的母亲正握着父亲的草帽当小扇,呼哧呼哧……她应和着:“可不是嘛,一遍又一遍,石磙都磨薄了,牛腿都走细了。俺家的朱先生是个讲究人,像给自己刮胡子净面一般细致……”母亲的赞许让父亲朗声大笑起来,像得了老师表扬的孩子,甜蜜而骄傲。
中午的日头有了威力,硬滑光洁的打麦场像被阳光打了一层蜡,白汪汪地泛着亮光,晃得几只蝴蝶像喝醉了似的,踉踉跄跄,欲落未落,生怕打滑摔了跤。
晚上,父亲又推着架子车来到打麦场,卸下车上的几个木水桶,和母亲两人各执水瓢,把场地细细泼洒了一遍。一趟又一趟,拉水,洒场。父亲说,压实的地面再洇一遍水,更硬实。
彼时,麦子的芒与路边的芒草上满是晶亮的露水,弯月的淡光,粉似的,敷在薄蓝的远天上,仿佛一碰就会被风吹落吹远的样子。母亲轻轻捶了捶有些酸疼的腰,鼻头上粉粉的汗珠欲落未落。父亲弯下身,两根手指并拢,轻轻地把母亲的汗珠刮了去,母亲未躲,指着月亮说:“多美的月儿呃!”父亲说:“像你的眉毛。”
月光下的打麦场挺了挺硬实的腰身,等着迎接收割后的麦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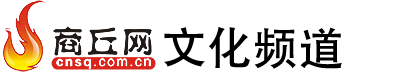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