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走了迅哥也走了,清明来了迅哥没再来。
迅哥,清明就要来了,这几天一直下雨,我很想你。
20年前,我们初次见面,也是一个雨天,已经忘记了在哪里,是开什么类型的会,只记得迅哥发言时大声说,今天有收获,认识了三耳教授。
那天,不喝酒的迅哥,喝了5小杯,我喝了5两。
很抱歉,见面前,我居然觉得迅哥是老弟。
2002年年底,我从商丘南下湛江,原计划潜心教书,不再写报刊评论。不料次年暑假后开学,晚报一位潇洒女记者上门,为副刊约稿,见面不说话,摸出一瓶白酒,一分为二。我就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千字文。那年10月19日,鲁迅忌日,我把一段讲义——“鲁迅研究”课的结束语整理出来,一看近三千字,太长了,就发给了湛江日报副刊信箱,记得题目叫《鲁迅的意义》。结尾是用鲁迅逝世4周年时郭沫若的话:“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10月26日,一个陌生电话打来:“是宋老师吗?我是日报文化版编辑陈迅,你的文章今天见报啦,我一个字没有改!”
他声音虽然有点沙哑,不太标准的“粤普”,但比较洪亮,我以为是中年编辑,表示了感谢,答应继续写稿。
那次开会一见如故,说的几乎全是杂文界的事情——他的不少作者、熟人我也熟识。我在《大河报》也是编评论版。
第二天,我到图书馆,找到他的《迅口开河》专栏,一口气读了十几篇,明白了他的仗义执言与文字功底。后来认识了报社河南老乡梦秋和她的闺蜜金凤,隔三岔五一起吃顿便饭,云天雾地聊一阵,很是爽快。
不管在哪里吃饭,迅哥很少打车,自行车是他的标配。他是地道的土著,长得很普通,不像作协的头头,像大队会计。他笑得很孩子气,与他文字的老到判若两人。
2013年11月,晚报编辑策划了一个类似“锵锵三人行”的对话式的评论版,让广西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小陈主持,我和迅哥做发言嘉宾,记得是每周一次。于是我们有了不断见面的机会,有时候也不见面,是把评论文字拢在一起,分层次变为聊天。
那一阵子,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与择业观念,政务网站如何便民利民,体育如何向“群众性”倾斜,“回家过年”为什么引发恐惧,赶“消费盛宴”值不值得,如何保证“破格提拔”公平性等社会热点,都成了我们的话题,有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
但是,也正因“切磋”得多,迅哥忧国忧民的赤诚、思想的锐利和谈锋的劲健留在了我的心底。例如有一阵网上流行不大文明的“屌丝体”,他认为很粗鄙,是生活平庸、感情空虚的宣泄。我说,对有些新词语应该稍加宽容。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自己也会偃旗息鼓。例如白话文,当初被复古派称为“引车卖浆之流”的土话,后来还是登堂入室。他不同意,引用孟子,说:人必先自侮然后人侮之。不可以“烂锅不怕摔”地去放大、展示丑陋。
再后来,报刊审读员老周不幸驭鹤,市文广新局让推荐一位对报刊比较熟悉的退休专家,我推荐了迅哥。开始有议论,说迅哥不是高级职称,是不是找个编审。我解释,报社不是高校,教授一抓一把,关键是对报纸的采写编评熟悉就行,不少新闻英语或者传媒管理学教授,恐怕连二三百字的“本报讯”也写不出来。就这样,我们又能够两三个月见一次面,嘘寒问暖。
最有印象的一次,是2015年国庆节过后,开审读会,集中说抗击台风“彩虹”。他头一句就说:“今天差点见不到诸位。”原来他家阳台的玻璃门栓不紧,15级飓风袭来,他和老伴只好用毛毯护住阳台门,夫妇再用身体顶住毛毯,前后一个多小时,累得几乎虚脱。我说:“你逃跑呀!玻璃烂了多危险!”他说一旦顶住了门,就忘记了还能跑。
记得2017年,我回老家商丘工学院执教,顺便照看母亲,走之前,我们还在一家小饭馆里见面,说好了“苟富贵,莫相忘”,回来就联系。不料那竟是最后一面。
今年2月初,几位报社朋友告诉我:迅哥走了。我不相信,他才70出头,那样有生命激情,整个港城都有他的自行车的轮印,怎么可能呢。后来看到日报副刊上何银华老师的《迅哥其人》,确信他走了,确信他的音容笑貌已经是历史。
如今,迅哥走后第一个清明就要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样说,只知道再也听不到迅哥用沙哑的声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
清明来了,乍暖还寒。迅哥,你在那边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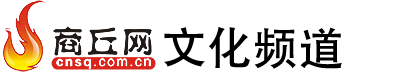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