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整理书房,移出书柜一角的纸箱,想必是旧书,打算作废物处理。可一倒出来,却是满箱的书信。一沓沓黄的、白的,长的、短的信封散落一地。
面对这些信件,恍若看见久违的朋友与曾经的自己,既亲切又有几分陌生。一阵悸动后,不由得蹲下身去,将它们一一拾起。继而,挪来一把椅子,端坐着,一封一封,细细地阅读。信的起止,从1979年到1999年,整整20载。要知道,17岁至37岁,那可是我的金色年华与青春岁月。此刻的我,情不自禁,边看信,边回忆,让思绪穿越时空,去尘封已久的脑海深处打捞远逝的故事。所以,读旧信,便是复读、回放自己的青春。透过字里行间,已然触摸到往日时光的印迹,让点点滴滴拼凑一起,成为充实当今生活的诗行与篇章。
信件类别,平信、挂号信、航空快信皆有。各色邮票面值不等,邮戳日期依稀可辨。信件对象涉及同学、亲友与学生,内容冗杂,谈学习、说工作、聊生活。其中,一大半信件是我写给他人的留底,言词有的婉转流丽,有的慷慨激昂。看来,自己也曾情感丰富、神采飞扬。读着读着,时而把自己招惹得惆怅满腹、黯然神伤,时而又把自己撩拨得心潮澎湃、血脉偾张。
看这一封最早的信,写给大哥的。洋洋洒洒几千字,信笺厚厚一叠,胀得信封鼓鼓囊囊。通读一遍,居然充斥人生感悟、处事心得等内容,俨然一副少年老成的口吻。再看这一封,是给一位学业受挫的学生的回信。满纸激励话语,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情真意切,看得自己都有几分感动。我那时候二十来岁,比学生大不了多少,既是老师,更像兄长。想起来,当时有那样的工作热情与爱生情怀,着实不易,欣慰无比。还有这一封来信,字体娟秀,语句矜持含蓄、柔美甜腻……如今再读,依然耳热心跳、浮想联翩。
信札里的一大摞,是与妻子的通信,去信回信放在一起。不过,那时还属女朋友。那年代,通信不发达,无手机,电话机也不多,双方的联络主要靠写信。我们的相处很传统,熟人介绍,目的明确,直抵谈婚论嫁。或许因为我家境贫寒、相貌平平,又一身土气,她有点不置可否。之后,我坚持每周寄信一封。我们虽然相隔只有15公里,可一封信从投进邮筒,到收到对方回信,一个来回得半个月之久。等信的滋味很奇妙,既期盼又焦虑,一听到邮差的自行车铃声,便显得急不可耐。待接到信的那一刻,就像收获劳动果实一般兴奋。这样一来二去,渐渐地,信越写越厚,相互称呼也由三个字变为两个字,最后一个字。再后来,自然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可以说,我与妻子的相识、相知、相恋到相守,书信是最好的媒介,功不可没。
我看信正酣,妻子过来,一眼认出了那封航空快信。这是1987年6月我在厦门短期学习时,从厦门大学寄给妻子的一封信。将信抽出,蓦然,几片干枯发黄的树叶从中滑落下来,伸手抓起,随即碎成粉末。原来,这是我当年从南普陀山顶摘下的相思树叶,夹在信件中寄给妻子的。展开书信,结尾处还赋五绝一首:“独坐普陀峰,思君意陡浓。折枝三片叶,遥寄我情钟。”诗与叶一起,以表思念之情。想不到,我理科男一枚,竟然也能做出一件浪漫事来。据说,妻子为这廉价的信物,感动了许久。
一整天,信大多浏览了一遍。便逐一掸去灰尘,重新分类捆扎、包裹,安放妥当。待日后寻暇再读,继续追忆曾经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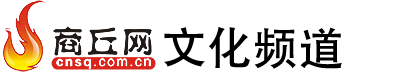


 商丘网
商丘网